一
多少年来,库布其这句蒙古语,常被人翻译为弓弦,意即黄河为弓,沙漠为弦。
居住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的莫日根道尔计跟我讲,幼年时他最爱做的事就是一次次爬上高高的沙丘,向外眺望着。幼时,小莫日根听老人们讲过许多黄河的传说,但从未见到过如弓的黄河。阿妈对他说,待他长大一点,就带他到黄河边上磕头去。在蒙古语中黄河被称为哈屯高勒,意即母亲河。库布其人守望黄河,就像守望母亲。
眼前不远的地方倒是有一汪清水,还有直伸到沙丘脚下的寸草滩。正是有了这汪碧水,这片草滩,这儿才被称为赛乌素才登,直译成汉语为有好水草的地方。但家乡那片好水,茵茵碧草只是留在莫日根道尔计幼时的记忆里,就像一个遥远的梦。
那是一场黑沙暴过后,小莫日根发现沙丘压上了他家房屋的后山墙,一群山羊跑上家里的房顶,凄凄地咩咩叫着。房顶缝隙处,窸窸地往下落着细沙。阿妈疯一般双手挥着红柳编的簸箕,刮着压在房顶上的沙子,屋子房梁发出“吱叽叽”的叫声,就像藏着一窝饿极的老鼠。阿爸一身风尘地赶回来,毅然决定扒掉门窗木料,选择一个高处,重砌草坯盖房。这时,小莫日根才发现平常羊儿们饮水的那汪清清的淖尔没有了,沙漠无情地吞噬了那片好水。
阿爸默默地不说话,在一处青草茂密的地方,默默地挖了一眼井,并用干枯的沙柳条子围了起来。羊儿又有水喝了,小莫日根觉得阿爸就是库布其沙漠上的罗汉金刚。莫日根道尔计记不得是哪年跟着父母在库布其沙漠上扒沙掏沙的。他冲我憨憨地笑着、思索着,是五岁还是七岁?“咳,六十多年了。”他感叹道。
二
那年,当小莫日根舞着双手开始像阿爸阿妈一样扒沙挖沙时,有一个叫徐治民的汉族大叔带着一支治沙队伍,开进了库布其沙漠东端一个叫园子塔拉的地方。但他们不是挖沙扒沙,是要把树、草栽种在荒无人烟的园子塔拉大荒漠里。园子塔拉原本是一片好草场,人们在这里开草原种庄稼,最后起沙了,远处的大沙漠,几场大风过后,突兀地出现在开荒的人们面前。他们扒掉门窗,用牛车载着锅碗瓢盆、铁锹犁杖,哼着“二姑舅捎来一句话,口外那儿有好收成……”继续走他们的西口了。这是典型的“游种”,开一片草场种几年地,一起沙子便拔腿就走,再寻新的草地开荒种地,鄂尔多斯人称之为“倒山种”。
“六月的沙蓬无根草,哪搭搭挂住哪搭搭好……”“倒山种”人们的歌声刺疼了徐治民。徐治民已经不是在口外揽工种地的受苦汉了,而是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的组长。老徐带领的这十几位翻身农民是库布其沙漠上第一代种树人。刚开始种树时,风沙大得能把人埋了,栽下的树苗全被沙压死。人们这才知道在沙漠上种树是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人们拨弄着埋在沙里的干枯树苗,不禁有些泄气。有人讥老徐:“你这是糟蹋五谷哩!”这是句很重的话,意即只吃饭不干正事。老徐不服气,他领着人们在大沙子的脚底下栽种沙蒿沙柳,苦干几年,他们栽活大片的沙蒿沙柳,终于挡住了沙头。
他领着人们冬天搞挡沙坝,春天栽沙柳,植树苗,旗里林业站的人还来专门科学指导,建设固沙植物网格,规划林田建设。为了保证林木的成活率,老徐还在园子塔拉打了多眼水井。春旱时,老徐就挑水浇树,老徐和乡亲们的肩膀头压出的老茧一层又一层。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徐领着人们在园子塔拉共营造了十八条林带,最长的有十五里。一眼望去绿油油的,浩瀚大漠中透出了绿的春意。许多“倒山种”的老户,又回到了园子塔拉,跟着老徐植树种草。终于,沙子欺负不动人,园子塔拉已是满目翠绿,老徐这才想起,要将自己的家搬进园子塔拉,屈指一算,这个弃家治沙的人,已经离开家整整七个年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六十多岁的徐治民仍继续带着乡亲们治沙种树,一排排小树苗“嗖嗖”往高蹿,老徐的腰却慢慢佝偻了。有一天,老徐一头跌倒在治沙工地上,大口大口往外喷血。
乡亲们心疼地说:“老徐这是撅着了。”
“撅着了”的老徐开始护树,守护这片林子,驱赶着窜入林地啃树的牲口。谁要是想动他一棵树,他跟人拼老命的心思都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为年届八旬的徐治民立了一块碑,碑文记录了徐治民老人四十年绿化沙漠的事迹。
1991年的春天,我专门去采访徐治民老人。那天,他不在家,我默默地看着老人简陋的土坯房,觉得辛苦种了一辈子树的老人应该过得更宽裕些。他老伴带我去见老人,路上他老伴告诉我,老徐这些日子心里麻、缠得慌,说是人们想分成材林换钱,老徐就是不同意。有人嫌他挡了财路,就在碑上乱写乱画。老徐很生气,有空就来碑前看看。果然我在碑前见到了徐治民老人,一个壮汉站在他身旁说着什么。老人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戴着顶深蓝色的帽子,佝偻着身子,脸板得就像一块石头。春天的阳光透过树的枝条斑驳弄影在他那苍老的脸上,壮汉几乎是冲他吼:“叔,你倒是说句话呀!”
他老伴悄声告诉我,这是老徐的侄子,侄子要建新房,想伐两株树,做门窗。已经磨老徐几天了,老伴也劝老徐道:“你倒是给孩子句话呀!”
老人就是不开口,侄子哑着嗓子说:“老叔,咱治几十年沙图了个甚?”
这的确是个问题。鄂尔多斯当时有这样的俚语:远看是讨吃要饭的,近看是治沙站的。还有这样的话: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那年,我采访库布其、毛乌素沙漠的治沙者们时,确实发现植树种草与富裕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那时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兴“念草木经,兴畜牧业”理念。伊克昭盟在鄂尔多斯实施“两翼一体”的发展战略,即治理荒漠化,美化绿化贫困山地、沙地,甚至为每户农牧民制定了林地、经济林、水浇地、牲畜的具体数目。各级政府和鄂尔多斯人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那时,大漠上,山地间,到处都是重新治理鄂尔多斯河山的壮士。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治理模式,呼唤着农牧民脱贫致富的雄心壮志,激励着更大范围的农牧民投身于生态恢复和建设美好家园中来。
那个沙尘暴不断的春天,我驱车行驶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深入到库布其、毛乌素沙漠治沙者的工地,准格尔山地小流域治理工地,感受这山河巨变,曾为茫茫沙漠上铺出的星点绿色,多次泪水盈眶。但贫穷的治沙者和治沙者的贫穷始终萦绕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库布其沙漠上成立了“库布其沙漠开发恩格贝试验区”,努力尝试一种新的治理荒漠化路子,力图拉近治沙与富裕的距离。后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也参与到这里来,也听说日本的治沙专家远山正瑛将其试验基地搬进了恩格贝。我在恩格贝见到了被日本人尊为“沙丘之父”的远山正瑛,他曾成功治理日本列岛的沿海沙丘。远山正瑛来恩格贝治沙试验区前,已在中国治沙多年,著名的沙坡头治沙工程,也有他的心血和智慧。
三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莫日根道尔计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
这个像他的父辈一样扒沙掏沙、守护家园已经几十年的他,也变成了沙漠上的铁打金刚。几十年来,莫日根道尔计和他的家人被沙漠撵得搬了多少次家他已记不清了,但他仍苦苦死守着赛乌素才登。他守望着这片浸染着先辈骨血的大沙漠,不屈不挠地在这片沙漠里扒沙挖沙固沙,像一匹吃苦耐劳的马一样守护耕耘着先人放牧的草地。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投入在库布其沙漠的腹地种出了七千多亩人工森林。其中红柳、沙柳、杨柴、柠条、沙棘等耐旱耐寒植物,还有无边无际的牧草,已经构起了自己的生态屏障。绿草地上,汪汪的湿地上积起了一片片碧水,茵茵青草向远方扩展,而逞威几百年的沙漠已不见踪影。莫日根道尔计带我站在一个高处,极目望着眼前这无尽绿色,感慨地对我说:“就跟做梦似的!”我默默地望着眼前这大海一般的翠绿,心想,沙漠去哪儿了呢?真像莫日根道尔计说的,这是在梦幻之中?
莫日根道尔计告诉我,他的造林治沙之路,是从二十年前参加穿沙公路的修建开始的。那时,饱受库布其沙漠之害的十万儿女,响应旗委、政府的号召,出钱出力,在人迹罕见的库布其沙漠上修筑了第一条穿沙公路。为了公路不被沙漠吞噬掉,旗委、政府下了死命令,要保护好这条生命线。公路两侧的固沙任务,分段包给了全旗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沿线的乡镇苏木。沿线的农牧民也都上了穿沙公路,出力出劳。
莫日根道尔计就是随着几万修路护路大军来到穿沙公路的。看着人们在林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沙漠上用枯柳、秸草制作方方整整的沙障,而且栽种上各类植被,在道路两边栽起树木,他感到很新鲜,他一直以为草木应是地上自然长出来的,原来草木在沙漠里还能人工种植。他想,我为什么不能在赛乌素才登种一种呢?草木固住了沙,就再也不会被风沙撵得满滩跑了,儿孙辈就不用像我这样把日子过得满头大汗。在护路工地上,莫日根道尔计学会了种植技术,回到赛乌素才登后,还试着在自己家房前屋后的大明沙上扎起了网格沙障,并在网格上栽种几百亩沙柳,冬去春来竟然活了不少。莫日根道尔计和家人连干五年,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硬是在大沙漠上种植了五千余亩人工林。终于,明沙也停止移动,莫日根道尔计高兴地对妻子乌日桑道:以后咱再也不用过翻窗出户的日子了。
在库布其沙漠,哪家哪户的屋门没被沙丘堵过,谁没有无奈翻窗出门的记忆呢?为了活下去,为了放牧的牛羊,库布其的人们修建草库伦,改建水浇地,种植人工林,在茫茫大漠上播撒着星星点点的绿色,在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尽管在库布其沙漠上出现了千百个像徐治民、莫日根道尔计这样的沙漠斗士,但库布其沙漠始终也没有摆脱“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生态怪圈。世纪之交那几年,鄂尔多斯市碰上了连续三年的大旱,大漠生烟。2001年,全市八千多万亩草场有一半没有返青,一千六百多万亩草场枯死。鄂尔多斯的沙尘暴越来越疯,被沙压死的牲畜越来越多,人们曾在一只被沙压住的活羊身上抖下二十多斤沙土来。
百折不挠,愈挫愈勇,严酷的大沙漠造就了库布其沙漠儿女的坚强性格。正当莫日根道尔计迎着风沙在自己刚栽的两千亩红柳林里清沙时,离赛乌素才登百余里之外的道图嘎查的蒙古族小伙子孟克达来遇上了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儿。他在荒漠中听到了轰轰隆隆的汽车发动机声。孟克达来急忙攀上高高的沙漠,踮脚眺望着,只见起伏的沙浪之间,上下跳跃着一辆汽车,就像颠簸在沙海上的一只小船。改革开放那年出生的孟克达来当然见过汽车,但在自己的家乡道图嘎查的大沙漠里还是头一次。汽车终于停在了道图海子边,只见车上下来一个中年大叔,看上去略显沧桑。
十八年后,已进中年的孟克达来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那人穿着一条红秋裤,挽到了大腿根上。后来,他才知道挽着裤腿下水的,是旗里的书记,人称白老汉。白老汉把道图海子看个透,还转了几个沙窝子,看望了一些世世代代窝在沙窝子里放羊的牧户。后来,孟克达来听牧民们议论,白老汉说了,这次下定决心要搞产业化治沙,不光治沙还要治穷。旗里要在这儿发展旅游业,牧民们牵着马儿让人遛一圈就能赚钱。不久又来了一些考察的人,搞勘测设计的,一拨又一拨,轰鸣的大小车辆生生在沙漠上碾出路来。
后来,王文彪带着亿利集团的人马来了。王文彪雄心十足要对道图海子沙漠实行整体开发,要在这里投资三十个亿建设国家级的沙漠地质公园。他给牧民们讲着道图海子的规划和未来,给大小道图海子更名为“七星湖”,意即对应天上的北斗七星。王文彪说自己也是库布其沙漠中走出的苦孩子,喝着黄河水、顶着库布其的风沙长大。他告诉道图嘎查的牧民们只要勤快,爱动脑筋,肯吃苦,每年挣个十几万不成问题。牧民们听着新鲜也略有狐疑:那还不是过上满房烧酒气的日子?天天炒米酥油和白糖,胡油烙饼炒鸡蛋?
经过多年的打造,“七星湖”现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备受关注的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永久地设立在这里。去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并发表了《鄂尔多斯宣言》。
现在道图海子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大沙漠披上了绿装,并已控制库布其流沙面积上千平方公里。亿利集团在这里建成了沙生植物研究中心,开辟了几十万亩甘草基地,沙柳基地,种植养殖基地,打通了多条沙漠公路。还有广阔的光伏发电项目,就像在沙漠上建造了一个绿色的湖泊。仅这一个项目投资就达二十七亿,现年发电收益可达一点五亿。光伏电板下搞起了种植养殖业,不时有鸡鹅从光伏电板绿荫下的草丛中蹿出。同样,这个项目可以安排上百户农牧民,进行光伏电板的擦拭维护工作以及板下绿地开展种植养殖业,许多国家级的贫困户从这里脱了贫走向富庶。
孟克达来是十年前搬进亿利集团道图嘎查移民新村的,这些年他的感受是要看沙漠得开着车往里面寻找了。我见到他时,他刚带着一对从广州来的青年男女乘越野车逛沙漠,按规定路线是一小时三百元,可这对青年人非要往见不到绿色的大沙漠里钻。孟克达来只得带着他们往原始沙漠深处钻。深漠腹地的沙漠现在恢复得也都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游客感到不够刺激,有些不满意,孟克达来不禁有些感叹:这些人咋了,见点绿色咋还不满意了呢?
孟克达来家的小院里,停着几辆供游客游玩的高轮子沙地车,一辆小轿车,孟克达来的坐骑是一辆丰田山地越野车,进城则换上另一坐骑——一辆小轿车。现在孟克达来想联络村里的一些搞旅游的农户组织个大漠旅行社,吃住行玩一条龙,把项目做大。谈到收益,他告诉我,像现在他这样每年旅游收入达三十万元以上的,有二十几户。收入达二十万元以上的有四十余户。孟克达来现在是新村的党支部书记,对全村的情况了如指掌。
像亿利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进入到治沙领域,给库布其沙漠的治理带来质的变化。产业化治沙靠的是政府引导,企业发挥资金、信息数据、科学管理、新技术应用方面的众多优势,努力把沙产业链拉长,以惠及沙漠地区的千家万户。库布其儿女创建的“库布其模式”横空出世,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现在库布其沙漠的治理实践告诉人们,科学地利用沙漠、呵护沙漠、精耕沙漠,是治理荒漠化的有效方式。在鄂尔多斯,无论是领导、专家,还是学者、企业家、沙漠治理者,都认为沙漠可以“变害为宝”。当荒漠化治理进入产业化时代,首先要科学地认识沙漠,去粗取精,提高治理区的林分和草分,万不可沉湎于眼前的绿色。当沙漠不再流动,不再侵害我们的生存空间时,我们尽量不去打扰沙漠的安静,而要静下心来,等待沙漠的自我修复。而研究沙漠的光能利用,了解沙漠的土壤构造以及降水周期变化,地下水位和地上风速的变化,了解沙漠动物昆虫菌类以及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活泼生命,才能使我们的产业化更加多元化和科学化。
四
库布其沙漠上的风干圪梁,原本是一片荒漠,几乎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光听这名字就让人发怵。赵永亮及其所创建的东达蒙古王企业,在这里投巨资进行荒漠化改造,使之巨变。而这一切都源于赵永亮在库布其沙漠上对于一株沙柳和一只獭兔的深度研究和开发利用。
沙柳是固沙的先锋植物,易在沙漠里成活,人类不加干预,它只有三年的生命期。沙柳生根较浅,只吸附地表水和土壤营养,发芽抽枝,可供草原食草动物啃噬和人类作为薪柴使用。它的根部积起薄土供沙生草类菌类生长,而三年后自身枯死。这是一种让人尊敬的植物,它不拼命扎根吸取深层地下水分,根须也不四处扩张夺取营养。而沙柳又有平茬复壮的习性,通过人类对沙柳平茬,它又可抽枝发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但由于经济价值不大,人们往往任其生死,沙漠上经常见到枯死的沙柳枝滚成团,人们背回烧火做饭。沙柳纤维长,韧性好,是建造高质量密度板的上佳材料。赵永亮于是花重金从德国购进先进、环保的热压高密度生产线。仅这一条生产线,就能够消化方圆三百平方公里内荒漠生产的沙柳。有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农牧民种沙柳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一条先进的生产线,带富了上万名沙柳种植户,保证了三百平方公里荒漠绿色常在。
我曾考察过“翻身村”和“乌兰壕村”两个沙柳种植基地,那里户均沙柳业的收入都在三万元以上,多的高达十万元以上。农牧民普遍使用了小巧的电动平茬机,六十多岁的沙柳种植户李文玉老人告诉我,连他都能掌握使用平茬机的方法,人们再也不用往手心里吐唾沫、抡老镢头平茬了。为了降低农牧民的运输成本,企业还在重点的沙柳基地建立了削片厂,就地将原料转化成半成品送往生产线。这样,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农牧民的收入,激励了农牧民种植沙柳的积极性。在绿色中获取财富,这是产业化引领荒漠化治理的独有魅力。
一株小小的沙柳,竟被赵永亮舞得风生水起……
在风干圪梁建立世界獭兔之都,是赵永亮心中的一个梦想。獭兔是从国外引进的,其皮毛绒厚密实,肉质细嫩,在国内外市场上销路很好。赵永亮经过多次考察、专家论证,决定在库布其沙漠投资打造世界级獭兔之都,选定的就是风干圪梁。这里光照充裕,冬季寒冷,夏季清爽,非常适合獭兔生长。除了皮毛、肉食,其他的产业链也很长。兔的内脏,可以喂貂。貂除皮毛价值外,其内脏可以喂狼,产生的粪便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可以改良沙漠土壤,提高土地肥力。这样,便可带动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等综合产业发展。现在在风干圪梁围绕兔子转的已经有一万多人,其中有科学家、动物学家、医学专家,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农牧民。标准化的兔舍,建得又高又大又宽敞,每幢兔舍旁都有同样宽敞明亮的家庭式养兔人住所。我问养兔人李鹏程,在这收入怎么样?他告诉我,过去他种了三十多亩地,刨去各类费用,每年也就收入个两三万块钱。十年前,来了风干圪梁,那时艰苦,铲平了大明沙盖兔舍,种草种树。后来包了一棚兔子,收入就上来了。八年来,年纯收入都在十万元以上。
现在的风干圪梁已经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方圆五十八平方公里被绿色覆盖,基本见不到明沙。而其带动的绿色产业已经辐射方圆三百公里。赵永亮认为绿色并不是句号,治理荒漠的产业化应是对绿色的深思熟虑、精耕细作,在绿色中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从而惠及这个产业链上的农牧民。
现在风干圪梁被赵永亮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风水梁。风水梁已是市政配套和教育医疗科研设施机构齐全、产业集中的现代化的小镇。现在镇上常住居民有两万余人,很多在赵永亮的公司里工作,随着沙产业的做大做强,其远景规划将建成容纳十二万人的沙产业城市。
神奇的风水梁,富裕的养兔人!库布其沙漠神话般的巨变,让人流连忘返。放眼望去,绿色涌来,而沙漠渐渐褪去。即使是大明沙,也在重重绿色的重压之下,改变了状态。在我目及之处,沙漠已由涌动的新月形链状,变成了静态的圆形穹顶状。库布其沙漠圆润了,已经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气势。根据水文气象统计,近十年,库布其沙漠的降水量在年二百零一至四百四十三毫米之间徘徊,大风扬沙天气在年均六次左右。比起治理前的“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降水在一百毫米以下的恶劣干旱天气,库布其沙漠的沙生植物已经具备了自然修复的气象水文条件。对治理区继续实行精耕,继续拉长产业链,使绿富同兴蓬勃涌动、同生共长。
在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沙漠科学馆,当我见到一粒沙子在显微镜下的状态时,不禁惊呆了:那是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等各种色彩的晶粒组合,就像一颗颗晶莹灿烂的宝石熠熠生辉。我猛然觉得,这仿佛预示着库布其沙漠的灿烂未来。是库布其的沙漠儿女给了库布其精气神,给了千古荒漠这般好容颜。库布其儿女精心守望着这美丽的家园,一往无前地辛勤建设着这幸福的家园。沙漠儿女敞开大海般的胸襟,拥抱着新时代的八面来风,科学地与沙漠共舞共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梦,为了金山银山般的绿水青山永驻人间!
哦,库布其哟库布其……
肖亦农;《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10日 24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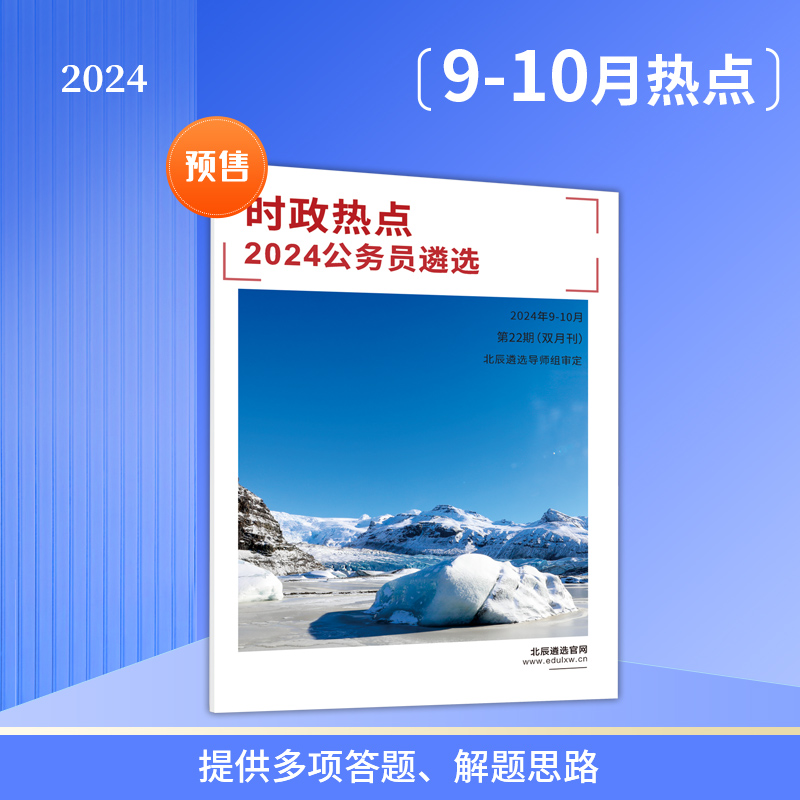







 (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

 支付宝
支付宝 微信
微信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