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泽东这首脍炙人口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于1930年,其中最易铭记的一句就是“十万工农下吉安”,经典的原因是“数字入诗”。“十万”工农不一定是实数,却展现了工农红军的浩大声势,诗眼在“十万”这个数字上。
“数字入诗”古亦有之,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会须一饮三百杯”、“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多作夸张、虚词使用。但像毛泽东这样频繁“数字入诗”,又用数字纪实的诗人并不多见。比如“二十万军重入赣”(《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七百里驱十五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故园三十二年前”(《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等等,都是用实际数字,准确记录革命斗争的场景或间隔的时间。
“数字入诗”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诗词中比比皆是,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统计,占比高达83.58%。这些数字、数据,是毛泽东胸中有“数”的直接表现。
毛泽东的胸中有“数”更多地展现在他的著作中,那些数字跟他青少年时期记录在家庭账簿上的收支一样,都是实打实的数据。
根据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八卷)》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分析:《毛泽东选集》收录158篇文章,《毛泽东文集》收录803 篇文章,共计 961篇。其中,用数字指导工作或阐明道理——即胸中有“数”的文章471 篇,占比 49.01%;如果从961篇文章中减去170篇电报、通讯、信件、祝词等这些简短的文章,胸中有“数”的文章就占59.55%,也即六成,可谓很高。特别是前期指导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文章,用数字摆事实、讲道理成为行文的一大特色,真可谓“无数字不文章”。
比如《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一文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共六百八十三。”
再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一文,毛泽东在揭示商人剥削、指导根据地贸易时也使用了准确的数字:“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又如《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一文,为了防止扩大富农的打击面,毛泽东就用数据进行了限制:“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可谓都用准确的数字指导工作。
这些指导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和政治方向的实际数字、数据,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都起到了“准绳”的作用,最后也上升到指导思想和方法的高度。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七条就是:胸中有数。他告诫全党“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他还用亲身体会告诉大家要掌握哪些数据:“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这段话是毛泽东对数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进一步强调,传达了“重视数据必得益于数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因为新中国的建设更需要胸中有“数”;而做到胸中有“数”,就是不能脱离调查研究,不能脱离群众。胸中有“数”的这个“数”也是真数,是实际数,绝不是虚假的数字。历史经验也证实,有了数据的“实”,才能求到真理的“是”,并且在“实”上求“是”的整个过程都会充满高度的自信,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里,就是“置顶”的豪情和“一览众山小”的磅礴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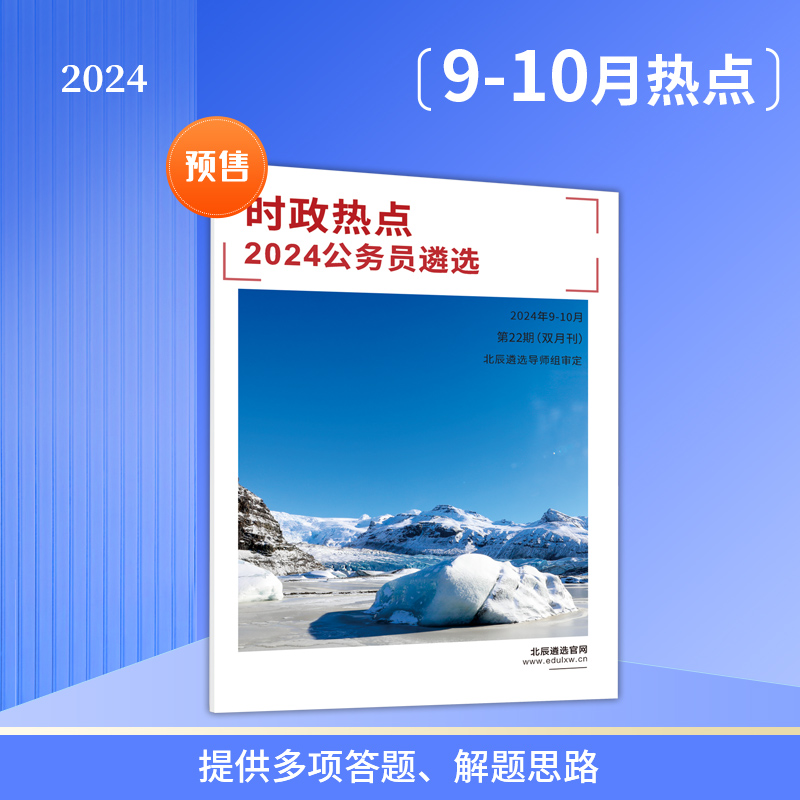







 (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

 支付宝
支付宝 微信
微信








.png)
















